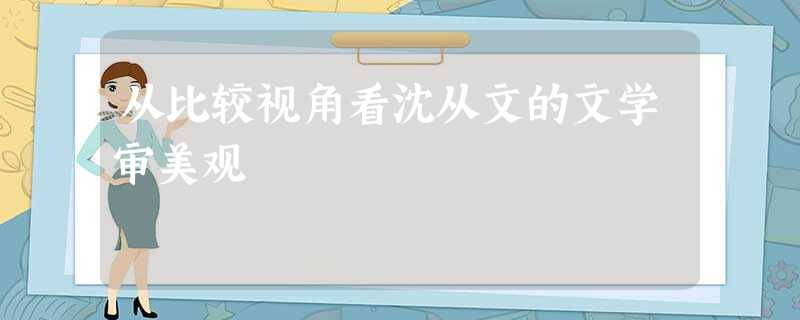关键词:沈从文 审美理想 审美愉悦
摘 要: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与尼采、叔本华感悟式的哲思具有某种相似性。但是,沈从文以自己的文本和话语方式对文学做出了独特的哲理阐释,表达了“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文学审美观念。
沈从文的文论著作,不仅语言形式上带有尼采和叔本华的直接感悟式色彩,而且内容上也与叔本华和尼采的“审美愉悦”具有关联性。
一
谈及《边城》创作动机,沈从文表达了渴望通过艺术创造去疏解生活压于情感的“沉忧与隐痛”:“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黏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回顾写作生涯,他一方面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之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另一方面又认为写作给自己带来了愉悦:“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他论及现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若将它建筑在一种抽象‘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与不幸。因为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以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他提出文学应超越现实:“人生应当还有个较高标准,至少还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几个标准。……因为不问别的如何,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澈‘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他所谓“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即摒除“道德的成见和商业的价值”,调动一切官能捕捉现象世界的各种美丽神奇的光影形线,按照“爱”与“美”的法则创造文学世界,让“人”的生命占有更大的空间和更长久的时间,用“美”来医治现实的创伤,让人们从个人的苦难中挣脱出来进而沉醉到文学的世界中去。他屡屡强调生命与生活的不同,强调生命的庄严、美丽与永恒,强调生命虽“随日月交替而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但它“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他相信,只有在审美的创造中,情感才可以摆脱呆滞沉重的肉体生活的干扰而“轻翥高飞,翱翔天外”。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尼采的“受痛苦者渴望美,也产生了美”的呼喊,似乎也证实着尼采所谓悲剧快感就是一种“玄思的安慰”,“尽管现象界在不断变动,但生命归根结底是美的,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等美学思想。
二
无论尼采、叔本华还是沈从文,只有以“世俗”道德的眼光观察世界时,他们才是悲观的;一旦以审美的目光观照人生时,他们都是乐观的。然而,作为“乐观主义”者,他们在相同中却有着差异。若说叔氏和尼氏都是极端的厌世者,其乐观只是哲学意义上对超越表象世界的无奈选择,而沈从文更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视角强调文学创作“美”的本质;若说叔氏、尼氏是从意志世界认为艺术是摆脱“原罪”的唯一通道,沈从文则是从中国都市与乡村的对比中发现现代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蠹蚀,从而渴望用艺术创作的美来拯救人性,恢复人类情感中失落已久的“哀乐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更接近卢梭和康德。卢梭认为,社会在发展理性的同时,违背了自然,造成了人自身的痛苦和不幸,所谓“出于造物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看到了文明社会的弊端,看到了人的自然感性生命在文明的规约下失去了本然的美。但人类毕竟不可能绝圣弃智,重回原始蒙昧时代。相比之下,康德对文明的批判更具现实性。虽然他也崇尚“自然”,但其“自然”是克服了文明病症之后的更高层次的自然回归。他认为,现代文明只是表面的文明,没能达到道德化的文明,他想通过文化为科学这只“独眼怪兽”安上另一只眼。
康德强调“表象”的意义,认为自然是存在的表象,艺术是对自然的摹写,自然是“真”,自然美是“善”的象征。这在叔本华、尼采及沈从文那里也被反复表述过,但他们的用意却有差异:康德是为了证明理性即“自在之物”的存在;叔本华是为了能“自在而欣然地放弃生命本身”,凭借“表象的愉悦”来忘记人生的痛苦;沈从文却力图以艺术创造的美来匡正人性的堕落,从而对“生命”做一种庄严神圣的解释。
叔本华、康德、沈从文都强调审美活动的无利害性,但康德归根到底是为了借审美来填平“知”和“行”的鸿沟,使人的道德理性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功能性的实现;叔本华、尼采是为了劝说人们弃绝“意志”的智慧,使由意志和情感构成的生命可以离开“意志的世界”而存在;沈从文则是以“乡下人”的立场,对“唯利唯实”、一切都为“迎拒取舍”而生存的庸俗人生观的否定。因此,他们虽然都具有“文明批判”的思想,但目的指向却不尽相同:三位西方哲人都是站在纯粹哲学的高度对文学的“玄思”,而沈从文则是站在艺术家的视角对文学所做的哲理阐释。
沈从文称自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在《一个人的自述》中,他自称:“爱旅行”、“常散步”、“有热情”、“很孤独”。
可见,耽于幻想、热爱自然生命、不断向自然和人生的远景凝眸、强烈的忧患意识构成了沈从文生命和创作历程的四大性格特征。这是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永远“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永远厌恶那些“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的“城里人”以及那些仅靠“应世技巧的圆熟”而取得“成功”的作家们的根本原因。这或许是沈从文倾其一生都在描绘和歌颂人的庄严永恒的生命,颂扬一切与自己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的根本原因。
三
若从文化学和结构主义批评视角审视,我们还会发现,沈从文的文学世界绝非色彩别异的生活画图,也非浅吟低唱的世外桃源之歌,而是作家对特异山水中具体生命形态的着力把握,是对特异生命形态的苦苦追思。而这种追思是在都市与湘西乡村、湘西乡村的过去与现在两种对比中加以显现的。从这种时空纵横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洞见沈从文热爱自然生命和批判现代文明的独特的审美理想。
沈从文喜爱把湘西的人事放在离别故乡多年的笔下去描绘。因此,影响他检视湘西山水的,固然有其不可忘怀的童年情结、区域文化培植出来的爱美天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现代都市人生的厌绝。在都市与乡村两种生命形态的对比中,沈从文发现,只有童年记忆里的湘西那原始朴野的生命形态,才是丰盈充沛、光彩浓烈、痛快淋漓的。他们总是任侠使性,大胆而为,大哭大歌,大爱大恨,生生死死,泰泰然然,全然与自然同律,处处显示着生命的本色本相。这里没有虚伪与矫情,没有阴谋与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是豪放庄严。相比之下,城里的人、事、人生形式却是那样的虚伪势利、唯利唯实!当然,在沈从文的理性视野中,湘西的人生形式也充满着悖论,那就是湘西人在将生与死、爱与怨、杀与被杀做等量齐观时,生命中美丽与坚韧的一面固然得到了张扬,但其残忍与脆弱的一面也得到了显现。这即是他在《湘西·凤凰》中所说的,“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神秘的背后隐藏了的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他认定,即便是残忍中的脆弱也绝无拖泥带水的僵态,也比都市的受现代文明奴役的黯淡苍白的人生形态可爱得多、美丽得多。可惜的是,这种美好的生命形式却在都市文明的浸染下一天天地走向衰亡,越来越呈现出“堕落”的趋势。为此,沈从文一面痛心疾首,一面愈加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审美理想、创作个性和特立独行的“乡下人”性情。他屡屡申明“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里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他宣称“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在‘神之解体的时代……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他声言“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代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他特别引进了“现在”与“未来”的概念,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越过“间隔城乡的深沟”,使人“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激起“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腐烂现实的怀疑”。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沈从文立足于征服和改造,悲观中孕育着乐观;而叔本华、尼采则是立足于厌弃和逃避,乐观中蕴含着绝对的悲观。
文学的重大功能之一是改造人的灵魂,而这种改造是通过创造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作为对实际生活的补充予以实现的。沈从文正是通过时空纵横两个维度的对比,力图为人们营造出一个健康、质朴、美丽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世界,用以挽住日益堕落的现实世界。这或许就是沈从文作品的全部人文精神之所在。
作者简介:李天福,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水云》,载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2]沈从文:《烛虚·三》,《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沈从文:《潜渊·六》,《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4]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5] 沈从文:《烛虚·五》,《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6] 沈从文:《潜渊·五》,《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7]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8] 沈从文:《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9] 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10]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11] 沈从文:《〈边城〉题记》,载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