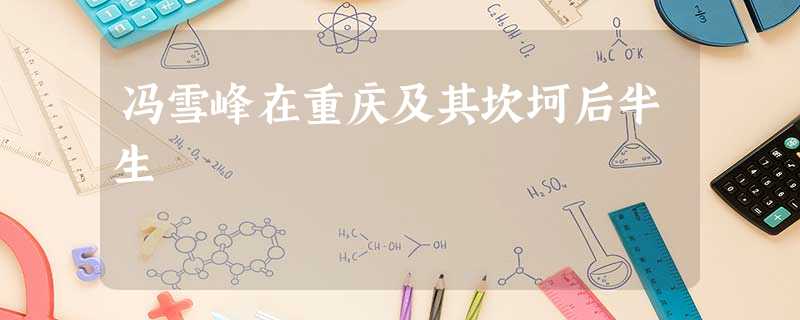颜坤琰
冯雪峰是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也是1930年代初期、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抗战后期,他经组织营救,从国民党上饶集中营保外就医,奉周恩来之召来到陪都重庆工作,在重庆生活了约两年零八个月。到重庆后,他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低调为人,勤奋做事,无畏面对国民党特务挑衅,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然而,他在重庆撰文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和耿直个性,却又为他坎坷的后半生埋下了多舛的祸根。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营救冯雪峰
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邀请艾青、韦嫈夫妇,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和舒群等几位著名文艺家,在延安杨家岭住地窑洞内座谈。为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萧军发言时,说了一段令人震惊的题外话。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并焦急地呼吁设法营救。
毛泽东听后惊诧地询问坐在他身旁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有人营救过没有?”回答是不知道。毛泽东立即指示陈云:“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延安来电后,立刻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案,决定由董必武出面,委托同为国民参政员的湖北籍小老乡胡秋原先生设法营救。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胡秋原欣然允诺,他很快向管辖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文友冯雪峰的电报,但顾祝同并没有买账。
冯雪峰的出狱,主要得力于他的中学同学、非党人士郭静唐的帮助。冯雪峰在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中说:“郭静唐在集中营里自始至终帮助我最大。”
郭静唐、冯雪峰同陷囹圄。1942年6月初,郭静唐的妻子找到国民党上层要人作保,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集中营释放了郭静唐。郭静唐获释后,并没有离开他早就盼望离开的集中营,而是千方百计要把冯雪峰也弄出来。
当集中营迁驻福建建阳徐市镇,郭静唐便为冯雪峰保外就医多方活动,但在建阳的活动却没有效果。于是他回到浙江老家,特地找到时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请他出面保释,黄绍竑答应帮忙。
1942年11月初,郭静唐带着黄绍竑的信函再次来到建阳,一心要将冯雪峰保释出狱。当时,重病在身的冯雪峰住在集中营的医务室。郭静唐找到特务头子张超交涉,张超提出“还要多找个人担保”。郭静唐无奈又去找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宦乡,请他一同具保冯雪峰出狱。宦乡听了郭静唐讲述的情况后,爽快地表示愿意担保。两个人商量后,联合具名写了张将冯雪峰“保外就医”的字据,张超在这张宦乡和郭静唐共同署名的具保书上,签字同意“交保外出治病,期限三个月”,并特别注明“三个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
冯雪峰的恢复自由,郭静唐、宦乡也功不可没。宦乡1989年2月逝世时,在新华社播发的北京举行宦乡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稿中(见1989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特别提到他“皖南事变后,曾利用当时的身份,从上饶集中营营救出冯雪峰等同志”。
1943年5月,冯雪峰辗转来到桂林,向当时在桂林负责文化界领导工作的邵荃麟汇报了被囚、出狱的经过。邵荃麟把他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派李亚群送来路费,让冯雪峰去重庆报到。
冯雪峰于1943年6月初到达重庆,暂时住在市郊化龙桥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第一个星期,他集中精力写被捕和出狱的经过材料,也写了他所知道的整个上饶集中营的情况。随后周恩来找他谈话,周恩来是很关心冯雪峰的,早在1942年底,上饶集中营里的林秋若被保释出狱后,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上饶集中营的情况时,周恩来就特别仔细地问她关于冯雪峰在狱中的情况。这次见面时,周恩来说他1937年在上海同博古争论所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但因此闹意气回到老家义乌去写小说是不应该的,并一再开导他,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要讲究方法,要提高斗争艺术。接着,周恩来指示他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写些文章,同时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关系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还指示他,为了能够公开活动,可以去找韩侍桁、姚蓬子和老舍等人解决住所问题。
为了避免国民党再次将冯雪峰投进监狱,冯雪峰的友人韩侍桁、老舍、姚蓬子联名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中宣部副部长兼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潘公展出据作保。韩侍桁又找了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向他言明,冯雪峰是个左翼文化人,曾被捕囚禁于上饶,到重庆来只是写写文章。萧与张、潘经过商量,同意冯雪峰公开露面。于是,7月间冯雪峰便移住韩侍桁家。两月后,又搬到了坐落在张家花园的“文协”会所。当时,管冯雪峰组织关系的是冯乃超,冯雪峰与冯乃超、徐冰编在一个党小组。这期间,他不时去曾家岩50号参加党小组会、看党内文件。后来,冯乃超等人觉得他住在“文协”既不利于工作,也不安全,认为还是应该按照周恩来指示,住到姚蓬子那里去比较好。于是,12月下旬,冯雪峰由冯乃超陪同,迁到了民国路(今重慶渝中区五一路)的作家书屋,在这里他一直住到离开重庆为止。
做“文协”与统战工作低调认真
冯雪峰到重庆后,虽然有人担保,以便让当局放心,但他处事依然谨小慎微。据胡风回忆,就在冯雪峰到渝的当月,张道藩在宴请“文协”和“文运会”(国民党官办文化组织)部分文艺家时,也邀请了冯雪峰出席。冯雪峰牢记周恩来的嘱咐:谨慎处事,低调为人。作家田仲济曾回忆当时的冯雪峰:“他还是以前在上海那样子,长长的面形,言谈很谦虚,经常喜欢穿一件长衫。他最大的特点是在任何场合不显示自己。不象有的人那样,一到了重庆就希望人人皆知,有会必到,有发言机会必讲,希望报纸发消息……”胡风夫人梅志也说:“这次见到他,就像是乡下来的老前辈,和蔼可亲。”
冯雪峰除了默默笔耕外,有时也出席“文协”的例会、恳谈会、读书会,他还做了不少幕后工作。1944年春节,张道藩要在“文协”年会上宣读一篇论文,指定文稿由茅盾、胡风、王平陵和李辰冬(李辰冬代表张道藩,并非“文协”理事)起草。胡风以“文协”研究部主任名义,当仁不让地争得论文起草权。胡风在文中除了写抗战和民主的内容外,竭力避开政治问题,提出文艺应该坚持反映抗战内容,应该和人民结合,应该展现文艺批评等等。这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胡风写好后,不仅给当时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冯乃超看,还特意把文稿拿到作家书屋请冯雪峰斟酌,就像当年左联时期一样,很多事情都要冯雪峰来把关。endprint
1945年初,作家骆宾基、丰村在丰都县被国民党县党部抓捕,并遭到严刑拷打,骆宾基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胡风遂赶到作家书屋,与冯雪峰商议施救事宜。冯雪峰虽然不能抛头露面,但他运筹帷幄,为两位作家的获释积极出谋划策,使得骆宾基、丰村终于在春节前夕获得了自由。
他不仅自己做统战工作,还教导年轻的同志也应去做统战工作。欧阳文彬是当时在亚美书店工作的一位年轻人,她从桂林调到重庆还不久,熟人不多,为了隐蔽的需要,不能和其他进步书店的同志们交往,亚美书店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又是国民党政府机关集中之处,接触到的多是国民党的公务员,不敢随便搭讪,因此感到憋闷,于是向冯雪峰诉苦。冯雪峰说,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控制相当严,“亚美”开设在国民党政府机关集中的上清寺地区,更应该利用这个特点,广交朋友,推广革命文化,让国民党的公务员多一个接触进步思想的机会。只要待人以诚,到处都会找到朋友。交朋友是为了扩大我们的队伍,增加我们的力量,而不是为了“解厌气”,或者为了个人有劲。冯雪峰的谈话给了欧阳文彬信心,她依照去做,不但书店有了起色,自己的心情也愉快开朗了,还结交了不少读者朋友。
勤奋写作 杂文受好评
在重庆的两年多时间,冯雪峰精力充沛地投入创作活动,进入了杂文创作的高峰期。
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抱病写了50多首长、短诗歌,他曾托人保管,后因环境恶劣这些诗作全部遗失了。到重庆后,冯雪峰根据自己所保存的不完整的底稿编辑成了一本诗集。原题为《真实之歌(荒野断抒上卷)》,共收诗作39首,另附《荒野的曙色》一诗的初稿《黎明》1首,由姚蓬子的作家书屋1943年12月出版,署名雪峰。该诗集下卷原是一首怀念友人的长诗《彗星》,但未能付梓和保存下来。
《真实之歌》的出版,在陪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当时也在重庆的作家聂绀弩读了这些正气冲天的长歌短诗,不禁针对那些无稽的诽语,表达自己对冯诗由衷的推崇,他在一首七言律诗中写道:“鲁迅文章画室(画室,冯雪峰的笔名)诗。”将鲁文和冯诗相提并论,评价极高。楼适夷在回忆文章《诗人冯雪峰》中写道:“他在重庆编辑出版的个人诗集《真实之歌》中的作品,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与《湖畔》及《春的歌集》不同,经过十多年血腥斗争的道路,他的思想感情的深度和诗的艺术的风格,已大大地发生了变化。如果过去的诗是青春的歌唱,那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则已变成为灵魂的悲烈的呼喊。”
在重庆期间,冯雪峰写得最多的是杂文。他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经历了上海的地下斗争,参加过苏区的反围剿,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经受了上饶集中营炼狱的考验,在苦难中更加坚毅和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说,进入中年期,才见到了人生的广阔和深远,对人生方理解到最深的意味,对社会、对历史、对真理的责任感特别深沉。
冯雪峰把他的所见所感都抒发在杂文中。“这时期的杂文,作者视野开阔,已从早期主要集中在文艺方面扩展到社会的种种世态,并向深层开掘。正如《乡风与市风》的书名所显示的,在空间上横跨当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既反映了乡村中的农民和妇女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又反映了都市中各色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动向;不仅如此,在时间上,还触及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富有历史的纵深感。作品的主题主要是对种种精神现象、社会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抨击各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意识、社会心理和民族的劣根性,赞美人民群众的质朴、倔强的灵魂和主宰历史命运的伟力,以及对文艺界存在的颓废、空虚和庸俗的精神状态的批判等。”(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他的雜文继承了鲁迅杂文的传统,以战斗性、思想性、政论性见长,反映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了19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富有时代特色。在不少篇什中,以敏锐的目光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对反动势力和腐朽的思想意识、社会心理与民族沉渣泛起,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强烈的憎恶。
冯雪峰的杂文大多发表在《文风杂志》月刊、《抗战文艺》《文艺杂志》《文萃》等刊物上。《文风杂志》为政治文化学术文艺的综合性期刊,1943年12月1日在重庆创刊,主编为韩侍桁,由重庆文风书局发行。冯雪峰与韩侍桁是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冯雪峰在韩家住过两个月,二人朝夕相处。韩侍桁在刊物筹办期间,即向冯雪峰约稿。冯雪峰给《文风杂志》先后提供了《谈片》《作于某城》《偶谈偶记》为题的三组共22篇杂文,是冯雪峰到重庆后发表杂文最多的一份刊物了。
冯雪峰将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杂文收编成3个集子。1943年1月至4月在丽水、小顺所写的杂文和8月至12月在重庆所写杂文结集为《乡风与市风》,共41篇,并序一篇,1944年11月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在重庆所写的杂文结集成《有进无退》,杂文30篇、序一篇,于1945年12月由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1945年11月至1946年7月作于重庆和上海的杂文结集成《跨的日子》,杂文49篇、序1篇,1946年9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冯雪峰杂文集的推出,获得了意外的好评,尤其是《乡风与市风》,甚至得到了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首肯。作家朱自清曾撰文评论《乡风与市风》:“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乡风与市风》可以说正是这种新作风的代表。”
与毛泽东会面
毛泽东飞抵重庆后,冯雪峰希望能见到分别多年的自己崇敬的领袖、战友、朋友,但他更关心毛泽东深入虎穴后的安危。据汤逊安回忆说,邵荃麟告诉了他和林秋若有关冯雪峰的两件事:一是雪峰最早获得蒋介石蓄意利用谈判的机会,企图把毛泽东长期软禁的情报,他迅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及早制订了逼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来回的有效措施。二是毛泽东与国民党进行紧张繁忙的谈判期间,还抽空读了冯雪峰所写的《乡风与市风》和《真实之歌》,并约冯雪峰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恳谈了一些时间,谈话中对上述两个集子给予了好评。(汤逊安《他首先是共产党人》,载《东海》1980年第1期)endprint
汤安逊在《毛主席与冯雪峰》(载《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一文中讲述:九月上旬的一个晚上,雪峰兴致冲冲地告诉我们说“我刚从山上回来,毛主席约我谈了许多话,我想不到主席在双方谈判那样紧张的关键时刻,还想到我这个和他分别了十年的小兵。他竟看过我最近发表的《奴隶与奴隶主义》,对我的文章评价很高,说是几年来他看到的文章中算是较好的一篇。”雪峰去见毛主席时,还特地穿了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和他告别时赠给他的那件旧青灰色的长衫,表示他是和秋白同志一道去见主席的。他谈到秋白不幸牺牲时,毛泽东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说,“秋白是个好同志,牺牲得太早太可惜了!”
又据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载《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记载:“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冯雪峰同志在重庆见到毛泽东同志。谈到文化工作方面的事时,毛泽东同志说:好几年来还没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友情是何等的深厚,冯雪峰的兴奋与激动就不难理解了。
多舛的后半生
1937年7月上旬,冯雪峰在上海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因对王明路线不满,与博古发生争执。9月中旬,冯雪峰写信给潘汉年请假,准备写作以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此后近两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包子衍编《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
1941年2月,冯雪峰在家乡神坛村被捕,囚禁于上饶集中营两年。1942年11月经营救,他得以治病名义被保释出狱,后赴重庆。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在《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一总题下,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摘录。共是三篇:《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和《文艺和政治》。
5月,文化界人士聚集郭沫若家,欢迎从延安来渝的何其芳和刘白羽。他俩是奉周恩来之命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重庆的,任务是介绍延安整风及文艺界情况。他俩按周恩来的指示,先向郭沫若谈延安整风及文艺界情况。郭沫若深受启发,即按周恩来在延安的嘱托,第二天就召开了座谈会,请诗人、小说家谈了延安整风情况、文艺座谈会前后及《讲话》精神。(《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这期间的某一天,聂绀弩到作家书屋去看望冯雪峰,碰巧胡风也在,两个人正议论周扬。聂绀弩插了一句:“无论你们怎样看不起周扬,周扬的理论总是和毛主席一致的。”胡风问:“你怎么知道?”
聂绀弩答:“这很简单,如果不一致,周扬就不会在延安搞得这么好。雪峰为什么搞不好呢?”冯雪峰跳起来,把手里的一本书砸到桌子上,大声说:“周扬有什么理论!”
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宣传毛泽东的《讲话》。在一次会议上,何其芳讲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如何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有听者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则忿忿地说:“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944年初,重庆《新华日报》转载《讲话》后,尤其是从延安来的何其芳和刘白羽宣讲和现身说法,在陪都进步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胡风、冯雪峰等人,都对《讲话》中的一些观点和何其芳的现身说法持有异议。
1945年下半年,陪都进步文艺界学习《讲话》,召开座谈会,总结回顾抗日战争以来的文艺运动,对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对因话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讨论中所产生的文艺与政治、思想性与艺术性、主观与客观等问题展开了争论,冯雪峰也应邀参加。他在“漫谈会”上作过一个长的发言,后来整理成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是冯雪峰理论著作中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46年1月20日至2月20日出版的《<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上。文章以他自己的革命实践,“总结过去的经验,明白现在的基础,决定今后的方向和工作”。全文共七章,论述了“五四”革命文学传统、革命的现实主义、统一战线、大众化和民族形式、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思想和现实等问题。
冯雪峰主观上认为他这篇文章是遵照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但他这篇文章在论述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时,论及作家在创作中的主观力或主观作用,当时就受到批评,有人认为他是提倡“唯心论”,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反对《讲话》中所提倡的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某评论家发表在1946年11月《文艺生活》上的《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一文中批評说:“我不能不首先声明,冯先生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基本看法,是与辩证唯物论有很大距离的。”(《文艺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陈涌的回忆文章中也说道:“这个发言,我看过后,有一次在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的面前说,这是反对胡风的,当时这个同志却立刻给我更正:‘这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是全国解放以前的事。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候,我的确将信将疑。但当我比较仔细地读过雪峰同志这篇论文以后,我总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得出雪峰同志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结论。”(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正如陈涌所说,从冯雪峰这篇文章中没有理由得出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结论。但是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谈到主观力,只讲了深入工农兵和改造世界观,因此就以为凡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讲到的都是禁区,都是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吴长华《冯雪峰的传奇人生》,文汇出版社,2012年1月版)
针对当时重庆演出的话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两个剧本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论争,冯雪峰应《新华日报》副刊文艺版编者的要求,于1946年1月20日写了《题外的话》一文,发表在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题外的话》中提出,不要用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而换成政治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说法,反对把政治性和艺术性抽象地割裂开来。冯雪峰指出,用政治标准第一或者艺术标准第一的方法来衡量评价艺术创作,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那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艺术创作引导到狭隘的道路上去。为此,他对艺术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标准,那就是统一的社会价值。(冯夏熊《关于雪峰》,载《回望雪峰》)endprint
他这篇文章发表仅20天,就立即受到批评。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刊出《关于现实主义》批评说,关于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什么“不明了”的地方,而冯雪峰反而“不明了”。话虽然说得委婉,但似乎暗指冯雪峰反对毛泽东在《讲话》中所主张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吴长华《冯雪峰的传奇人生》)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讲话》的反应1946年5月,何其芳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在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和《题外的话》两篇文章所宣扬的文艺观,与《讲话》精神相悖时,很是反感。
丁玲《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1948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指《跨的日子》)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第8页)這个记载说明至少从1948年起,毛泽东已认为冯雪峰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泽东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极为反感。
冯雪峰对《讲话》的态度,他与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一些“分歧”,冯雪峰与部分文人的矛盾及耿直的个性,为他后半生的多舛埋下祸根。
1950年,冯雪峰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后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冯雪峰开始受到批判的导火索,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给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引起的。该评《红楼梦》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冯雪峰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
冯雪峰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次年被开除党籍,被迫中止公开的文学活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对冯雪峰作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彻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结论。
“文革”中冯雪峰受到冲击,被诬为叛徒,并下放到五七干校。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因病去世。在病重时,他曾对儿子冯夏熊诉说:“我没有能活着回到党的队伍里来……我心里难过!”逝世的前两天,他仍对前来看望的骆宾基说:“……我郑重要求:要回到党的队伍当中来,作一名列兵……”
1979年,中共中央为冯雪峰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