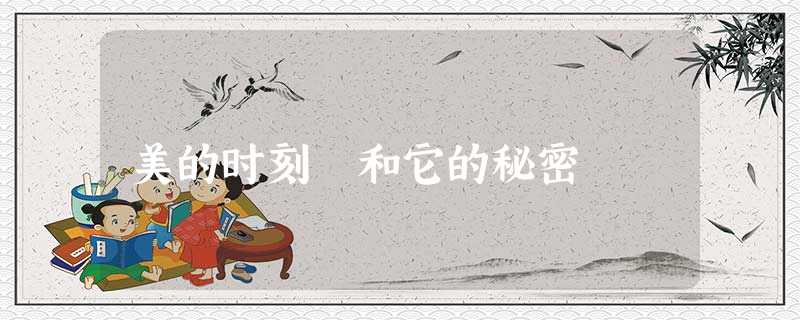韩松刚
孙频的小说一直在变。从《松林夜宴图》,到《我们骑鲸而去》,再到《以鸟兽之名》,甚至于更近的《诸神的北方》,这种变几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果说,在《松林夜宴图》中,孙频试图通过艺术抵达历史的景深,在《鲛在水中央》中,通过叙事的轻描淡写,去对抗一种巨大的悲伤,那么在《我们骑鲸而去》中,则是借助于“戏剧”探寻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在《以鸟兽之名》中,又一掉头,把视角伸向了人与山林——一个更大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命题,而《诸神的北方》将这一命题做了继续的想象和深入。
与早期小说中那横冲直撞的“凶狠”相比,孙频近期的小说越发平和而忧伤。她好像忽然之间又掌握了小说的新魔法,在一个个让人生死攸关的时刻,赋予生命以美的力量和诗的意义。比如《诸神的北方》中,对于母亲的自杀,小说写道:“找到她的尸体是在第二天上午,她在昨晚卧轨自杀了。她独自一人踏着月光,在旷野里走了十里路,然后坐在铁轨上耐心等着那辆半夜过路的火车。火车准点来了,在黑暗的旷野里,远远就能看到一个呼啸的火车头带领着一串明亮的小房子奔跑而来,那群小房子快乐极了,驮着旅人们的各种梦境。她死的时候只穿着一只鞋,另一只鞋并不在铁轨旁边,应该是她在旷野里赶路的时候,那只鞋就已经丢掉了,只是她浑然不觉,继续在月光下赶路。”
孙频的这段描写,让我不期然想起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臥轨自杀的安娜。这是两个截然逆反的女性角色。一个因爱而生,一个为尊严而战;一个为爱失去了理性,一个与生活展开着搏斗;一个以死向世人宣誓,一个通过死获取尘世的安慰。但她们也有共通的地方,她们都善良、充满了同情心,她们都受制于道德的牵绊和情感的内疚,而选择了一样的死亡方式。托翁笔下的安娜是迷人的,孙频笔下的“母亲”,同样让人动容,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女性形象。她的死,凄凉而唯美,那一寂静的时刻,连同它的秘密,一起被带走了。这是孙频小说走向心灵内部的“情感”时刻。在阅读过程中,也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我感觉到孙频小说内部的结构开始发生了新的位移,一切的矛盾、纠葛、爱恨几乎都变得心照不宣起来。孙频深谙一个小说家的职责,就是用其情感、思想、技法去建立一个个美的时刻,并由此建构起一个个小说的秘密世界,而不是去呈现某种虚假的真实,或者缔造某种人为的“神话”。
但对于小说来说,要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仅仅有人物是不够的,它还要求创造一个关于世界的幻象,并在这种虚构中去实现时间的感觉。对于自己早期的小说创作,孙频也一直在反思。她最近的一系列小说,可以看作是反思自身的强烈实践。孙频似乎对她早期的小说经验、叙事手法和思想表达不停地进行反驳和改造,以期实现一种自我革新或者脱胎换骨。这是一个艰苦、煎熬的时刻。也是在这样的时刻里,美开始发酵,秘密开始呈现。她对世界的认识开始告别一种痛痒的直接碰触,而转入一种理性的、阔大的想象视域。她依旧清醒而固执,但显然已经走出了情绪的困顿天地。
读孙频的小说集《以鸟兽之名》,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认识到,小说是一次次持久而有力的审美颠覆。这是小说的艺术之道,也是价值所在。集中诸篇《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从整体的小说构架,到具体的叙事执行,再到思想的艺术表达,都透着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写作真义。这三篇小说,有着许多共同点,可以当作是孙频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新的系统表现。是的,思想性,这是孙频小说十分重要的品质和特征。正如何平教授在谈论《我们骑鲸而去》时所言:“思想性或者说哲思,我们现在很少用来谈论小说,尤其是对年轻作家的小说,但这可能却是孙频最近这些年有意为之去尝试的。”那么,孙频小说的思想性是如何达成的呢?在生与死中展开、实现。这是写作的基本主题,也是孙频多年执念的东西。《以鸟兽之名》,有一张凶杀案的外衣,但内里还是关于生和死,关于人的痛苦和命运。《骑白马者》,依赖于我对“田利生”的寻找,其实还是探讨的人的生命与存在、艰难和自由。《天物墟》,则是在废弃的村庄中,去发现文明得以生息、万物得以生长的秘密,以此来实现对于自然、历史、生命的综合思考。可以说,正是在思想性的关于生与死的演绎中,孙频继续并丰富着她的小说之旅,这是她的小说摆脱几乎静默的心理空间,开始走向更为纷杂的“孤独”的“思想”时刻。这样的时刻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夕阳开始慢慢落山,光线变得迟钝而柔和。一个枯瘦的老汉披着一身霞光回头看了看落日,脸上被染得金光闪闪,他长叹了一声,又把一天用完了呵。众人如石像一般,沐浴着晚霞,都久久不动。只消片刻,落日便完全坠入山谷,暮色变得苍茫起来,众人陆续起身,开始慢慢回巢。”(《以鸟兽之名》)“我恍惚间有一种时光在倒流的错觉,觉得自己正朝着过去走去,也许在这深山里走着走着便碰到了过去的自己,还或许走着走着便碰到了我的父亲,他那么年轻,还没有受到生活的任何摧残,而我还只是那个七岁的小孩子,一切都还来得及。”(《天物墟》)
从城市走入山林,孙频的转向让不少人着实吃了一惊。但细数孙频的小说之路,从《松林夜宴图》开始,她其实已经在做着一些有意的探索和尝试。只不过,到了小说集《以鸟兽之名》中,这种小说艺术的整体性更为凸显。孙频开始迷恋山林、向往自然,她笔下的风景和人也突然变得诗意盎然,这在早期的小说中并不多见。“森林从车窗外成片成片地掠过,一幕又一幕,连接成了一部流动的绿色电影,不时有鸟叫和花香扑面而来,走着走着,前面的峭壁上忽然跳出一枝火红色的野花,倚在陡峭处,妖媚地斜视着我们。河流若隐若现,时断时续地跟着我们。在开阔处,河流会忽然钻出来,两边芳草夹岸,河流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在山林茂密处,河流会忽然隐身不见,但就是在见不到河流身影的地方,依然能听到漫山遍野都是淙淙的流水声。”(《以鸟兽之名》)“河流在视野里若隐若现,即使钻进了河柳丛里踪迹全无,仍然可以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就在咫尺。走着走着,河流冷不丁又冒了出来,活泼泼地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河流两边青草夹岸,蒲公英携伞飞行。偶尔有白色的巨石挡在河道中间,河流也是欢快地侧身而过,并不上前挑衅。”(《骑白马者》)这样的风景描写,在小说集《以鸟兽之名》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孙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景物的描写充满了美学的耐心和诗意的想象。各种自然事物相互交织,成为小说的叙事背景,也成为一种虚构的经验幻象。这些基本的幻象吸引着读者,去与现实、生命进行对接,以使这些具有暗示性的词语超出其本身的意象,而具有了另一种复杂的情感内容。
我相信,孙频是试图在自然中让人获得某种解放。“自然的解放,就是重新恢复自然中促动生命的力量,就是重新恢复在那种徒劳于永无休止的竞争活动中不可能存在的感性的审美性能,正是这些审美的性能揭示出自由的嶄新性质。” 但事实上,在这些自然的、美的时刻背后,仍然有它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人被时代遗弃之后,那巨大的孤独几乎是无法消解的。故乡的重返,是为了摆脱孤独,但荒谬的是,在故乡的流浪中,更深重的孤独一阵阵袭来。不管是作为叙事者的“我”,还是他人,都无一能够幸免。“他简直像个国王一样,每天晚上等所有的人都下了班,这整栋楼都成了他一个人的疆域。他办公室里的那点灯光一直压迫着我,我担心他写着写着会忽然变成一只庞然大物,然后绝尘而去。而我则被遗弃在原地,变得越来越颓败平庸,最后彻底淹没在人群里。”(《以鸟兽之名》)“夕阳落山之后,夜色从旷野里升起,渐渐弥漫到了胡同口,老王站起来,把剩下的棒棒糖又戳回嘴里,然后背着两只手,慢慢朝玉林苑走去。其他人也陆续开始回巢,有人叹了一句,租房子做小买卖的不好过吧,住楼房领退休金的也不好过。”(《诸神的北方》)
但我不会因为孙频把写作的视野转向了山林,就贸然将她归入自然主义文学或当下热门的生态文学队伍中去,我想,孙频还是现代的,一种坚实的“流动的现代性”品质,永远是她小说的精魂。不过,孙频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现代性”同样充满了颇具现代意味的警惕和思考。这种警惕在《以鸟兽之名》中,是对自然世界的敬畏和信赖。“对山民来说,大山是一种宗教般的存在,山上所有的鸟兽草木,所有的风俗习惯都是我们的避难所。”在《骑白马者》中,是对历史浩茫的迷人想象和洞察,“这时候我已经敢肯定,这个村庄是有秘密的。不过,在这大山里,每道褶皱里都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有的秘密如林间草木一样,从长大、凋零到腐朽,都不会有人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有的秘密如山间蛰伏的猛兽,即使离得很远,你也能从空气中嗅到它们身上的气味。”而在《诸神的北方》中,则是对传统“秩序”的留恋,“我甚至开始想念这里的秩序,在我年少时候曾十分鄙弃的那些秩序和风俗,我后来一一开始怀念。这里不止有日月星辰的运行,还有各种神灵与鬼魂的出没,一个神灵、人、鬼魂共栖的空间不仅显得热闹,还十分浪漫,就像个大家族一样,墙上挂着各种规矩和禁忌,因为有了禁忌,便可生出不少敬畏。”
事实上,在喧嚣的时代背景中,由故土消失、家族分裂所带来的陌生情感让我们变得更加恐惧和不安,这种不安对艺术包括小说提出了一种想象力的挑战,就是我们如何在一种艺术的形式中去表现、体会、消化这些情感。小说在当下的意义,可能也在于此。它试图去创造一个更加广阔的虚幻空间,去容纳这些消化不良的情绪和情感,它形式可以是灵活,简单的、复杂的,结构可以是多变,线性的、复调的,它是发展的、丰富的,它以各种“现代性”的特征为生命提供真诚、主题和可能,并推动生活幻象的当代再现。孙频在一次和罗昕的对谈中说到:“我认为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有真诚可言的,在于它是有心跳和体温的生命体,有真正动人的东西凝结在里面,而不是经过粉饰的扭捏作态的‘假声’或‘圣徒’。我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看到了不同的风景,这些风景未必都尽如人意,而且并不是一种固态的存在,但都有着独特的生命力,我愿真诚地把每一个阶段有限的认知都写出来。”
孙频的小说与之前相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强化了“动”的可能性,不管是小说题目“我们骑鲸而去”“骑白马者”,还是小说中人物的不停游走,都具有这样一种品质。她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变动不居,以及人在各种力量围困之下那同样变幻莫测的孤独命运,和这些命运所显示出的各式各样的华丽而凄美的舞姿。“一个真正的艺术幻象,一个‘各种力’的王国,在那里,发散着生命力的纯想象的人们,正通过有吸引力的身、心活动,创造了一个动态形式的整体世界。”
孙频的小说向来充满了争议。但我们要承认,在80后作家中,孙频是少有的对“自身”进行反抗的小说写作者。她敢于放弃自身营造的各种紧迫性,甚至于完全离开惯常的审美维度,义无反顾地鱼跃到更加广阔的精神地带之中。她似乎深信,在小说的写作实践中,一定存在某种别样的叙事方式,可以唤醒一件事物,可以成为一种声音,可以实现一个时刻。